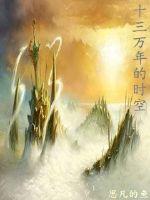书生与郎中很快便先张大老板一步离开了这一段昏暗的地方,而且在这徽州城中的大道上行走,越往城中走才越让人感受到徽州城的古朴,街道上严丝合缝般铺就的青石板已不知历经过多少雨雪风霜,但也正因如此,这些青石板在月光下熠熠生辉。
郎中背着古朴的木质药箱,看着书生心不在焉,脚步虚浮,甚至郎中几次抛出话题,书生也只是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话,显得甚是敷衍,不是哦,就是嗯,或者干脆在问,你说什么?而像郎中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很能耐得住自己的性子。
丑时已过,城中的百姓大多已入梦乡,彻夜不眠,随风摇曳的烛光仿佛在不停地诉说着徽州城一段又一段过往,灯火不灭,古城永存。
二人走至一处酒馆,郎中忽然止步,笑而不语。
而书生也随之停下脚步,只是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依旧有些出神,这时,一阵酒香飘过,身旁的郎中分明没有说话,而书生却忽然问郎中道:“你说喝酒?”
郎中愣了一下,如遭雷击,他瞥了眼书生斩钉截铁道:“喝!”
丑时以后,酒馆的人就像青楼一样,络绎不绝,只不过来酒馆的人大都只为了第二天睡得踏实些,而去青楼的人却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睡的踏实,他们宁愿自己睡的不踏实,也不想让身旁的人睡的踏实,否则银子便花的很是不值当。
两人忘了一眼此间酒馆的酒水价,并没有走进身侧这家酒馆,而是不约而同的继续顺着街道前行,慢慢悠悠的走进一条名叫李磨的深巷,巷子中酒馆很多,而郎中与书生却挑了间客人并不多的酒馆走了进去。
“小二,上酒。”
从进门到落座,都未看到酒馆老板的身影,只有一个小二打扮的年轻人时值深夜依旧很热情,很敬业,先是将桌子擦拭干净,又弯着腰道:“二位客官,喝点什么酒?”
郎中想了想,“越烈越好。”
书生皱起眉头,“米酒有吗?”
其实对于想买醉的人来说,像米酒这种毫无酒性可言的,无疑是最不会被选择的一种,郎中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不解的问道:“孔兄?”
书生摇了摇头,叹道:“对于只想喝醉的人来说,喝什么酒又有什么区别,喝多少又有什么区别?”
每当书生说出这种绕口的话,郎中总是无言以对,只是吩咐小二道:“一壶烧刀子,一坛米酒。”
“得嘞,二位客官稍等。”
不多时,小二已将酒从后厨端了出来。
郎中给自己倒了满满一碗后,又问小二要了碟花生米,不多不少,刚够一个人吃,这绝不是郎中吝啬,而是郎中觉得,此时的书生,再美味的下酒菜与糟糠也没甚区别。
书生毫不客气的抓了一把花生米塞进嘴里,咀嚼一阵子后,又双手抱起酒坛,咕咚咕咚喝了一会儿,随后将酒坛重重的放在桌上,“嘭”的一声,酒水甚至都溅了出来,不知书生是不是很久没有这么痛快饮酒的缘故,竟咳嗽了起来。
郎中笑道:“莫急莫急,此间无人与你争抢。”
就连倚靠在柱子上的小二也不禁莞尔。
不料,书生突然破口大骂道:“铜臭,一身的铜臭!”
小二很懂事,自知接下来的话他不该听,索性走出了酒馆。
郎中慢慢悠悠的饮下一杯,烧刀子特有的冲劲呛得他几乎流下眼泪,道:“孔兄说的极是。”
书生欲言又止,干脆提起另外一件事,道:“长生殿跟此事可有瓜葛?”
郎中认真道:“你我二人与长生殿门人虽然并不太熟络,但这么多年来,却也从未听到长生殿会使如此骇人听闻的手段,老夫听说那长生殿的曹九思最近也在调查此事,只是不知道是故意掩人耳目,还是……”说到这里,郎中饶有深意的望向书生。
书生回过神,重重道:“我宁可相信长生殿,也绝不相信凌苍穹。”
郎中顿时大吃一惊,慌忙起身道,“孔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书生冷哼一声道:“我孔家,莫兄你自然知晓,可莫兄不了解的其中的秘辛,委实太多了,若不是今天看到凌云视人命如草芥,张大老板助纣为虐,在下也绝不会将那些陈年旧事给翻出来。”
郎中望着门外,忽然警惕道:“孔兄,稍等。”
书生知他要做什么,所以并未询问,也并未拦着。
不过片刻,郎中已将门外的小二扶了进来,而小二已沉沉睡去。
书生再狂饮一口,眼神忽然变颓然,仿佛是想到了什么不敢轻易去想起的回忆。
郎中沉声问道:“孔兄家里难道真跟长生殿有勾结?”
酒劲儿尚在,书生抖然严肃道:“不错,长生殿成就了我孔家。”
郎中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惊讶,此事他也大概了解一些,毕竟当年孔家的罪状中就有一条,勾结魔教,而郎中眼前的这位孔先生选择藏身徽州城的原因便是如此,毕竟就目前而言,书生也只能在这徽州城隐姓埋名,苟活于世罢了。
郎中叹道:“不错,徽州城保护了不该保护的人,却也保护了该保护的人。”
书生接着回忆道:“那年,我不过双十年纪,恰好跟着表姐来到徽州城中,才免于劫难。”
郎中看着书生眼角的泪光,不忍道:“喝酒吧,那些陈年往事,不提也罢。”
书生怒气填胸,狠狠道:“非也,何谓欲加之罪,何谓何患无辞,我孔家与长生殿有交情不假,可我孔家之人,哪个不是一生只与青灯黄卷相伴,哪个又曾勾结魔教残害正道之士?”
郎中疑问道:“老夫依稀记得当年,他们的说辞是孔家二公子与长生殿女弟子私定终生,并且……才惹得那些山上的人不高兴,所以才…”
听到这里, 书生立刻打断郎中,怒骂道:“放他娘的十八代祖宗的屁!”
郎中怔了一阵,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书生如此,哪怕有人在书生眼前谈及数十年前的往事,书生也是神色自若,不像此刻。
突然之间,书生一手提起酒坛,一手沾着酒水,舞动手指,于虚空之中写下数字。
“苍穹之下,岂有完卵?”
郎中屏住呼吸,一字字的默念完毕,然后看着漫天的水雾缓缓消散,顿时如遭雷劈,仅这苍穹二字,足以让郎中明白一切。
书生哈哈笑道:“莫兄说的魔教女子,不正是凌城主的四夫人么?”
郎中大惊失色,“什么?”
书生娓娓道来:“莫兄有所不知,我二哥与二嫂相识已是四十年前,想当年,他们二人一见钟情,我二嫂家境贫寒,却也是个正经人家,虽然我等读书人向来讲究门当户对,但老爷子并不反对此事,没多久,家里便开始张罗迎娶的事宜了,谁知那日,二哥与带着二嫂来这徽州城散心之时,恰好碰到凌苍穹……”
说到这里,书生突然咳嗽不止。
郎中已然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想必是那凌苍穹觊觎二夫人美色,但又碍于身份,只能动了杀心。”
书生叹息道:“不错,可怜我二哥,只不过与长生殿门人见过一次,便被冠上与长生殿勾结的罪名。”
郎中干脆拿起酒壶,一饮而尽。
书生苦笑道:“深仇大恨,何时可报?”
郎中讶异道:“所以你便想利用张大老板,给你一次接近凌苍穹的机会?”
书生朗声道:“我已练剑二十余载,只盼有这么一个机会。”
郎中神情复杂,有些话不知该不该直接告诉自己这个知己。
书生似乎看出来郎中欲言又止,直接了当道:“莫兄,有什么话直说无妨。”
郎中摇摇头道,“孔兄如此行径,只怕与送死无疑。”
书生视死如归,“明知是死,那又如何?”
郎中严肃道:“深仇大恨,不可不报,但也需报的彻底。”
书生急忙请教道: “莫兄所言,怎么个彻底法?”
郎中勾起嘴角,压低嗓音道:“何不让整个凌家都被连根拔起,让凌氏一族直接消失于天地之间,有仇报仇,有怨报怨,我想除了孔兄,应该还有很多人都跟凌家有着深仇大恨,孔兄应该想办法联合他们,一起将凌家置于死地,到那个时候,你就算不杀凌苍穹,他也无颜面活在世上。”
书生面色潮红,激动道:“那依莫兄所言,在下该如何去做?”
郎中为难道:“就是不知,孔兄愿意付什么样的代价?”
书生掷地有声道:“一切!”
郎中手拈须,随即从药箱中取出一个深紫色的瓷瓶,道:“想办法让凌苍穹喝下去,大事可成。”
书生犹豫很久,忽然一把接过,然后才问道:“莫兄为何如此帮我?”
郎中悲从中来,咬牙切齿道:“我虽然与那凌苍穹并无仇恨,但那凌云,不过一条凌家的狗,竟杀我妻儿,此仇不报,我莫问誓不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