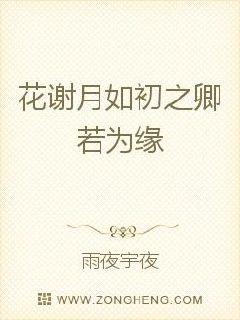第十八章 底牌尽出
楼玉宇离开婵心苑,立即前往梅心苑,吉祥把他迎进门。
进去时,薛诗采正在用膳,见楼玉宇进来,便让人把饭菜撤了。
“今儿怎的有空过来?”薛诗采可不认为楼玉宇是来陪她聊天的。
“我这次来是想跟常宣说说上次,我们未说完的事,”楼玉宇想薛诗采应该也等他这句话很久了。
“你们都退下吧,我与楼玉宇说说话,”薛诗采把身边伺候的人都支使了出去,才安心的楼玉宇继续这个话题:“那莫承欢已经准备好了?”
“只欠你这一东风了,”楼玉宇笑得邪气,笑得狡猾。
过了几日,到了何冲启程前往南部的日子,东天极让薛世章送行,早先已经商量安排过的,何冲出了城门便跟着商队走鑫通货运路。
何冲走后的两日,大街小巷流传着一种疯狂的谣言说这何冲名义上是去镇压,实际上是去赈灾的,何冲在出发前,曾召集他所有的乡绅富豪筹款募资,被他真的筹集到了不少的银两。
还说这何冲不知何时结识那鑫通商行的主事人,竟说服了鑫通帮其从凤兰运送粮食,此谣言一石激起千层浪,司马家与莫家的人都纷纷慌了神,这事若是真如传言所说,一旦让何冲赈灾成功,那整个南部三省都会落入薛世章手中,要知道,这南部三省一直都是苍雷最重要的军事要塞。
苍雷最大的水军部队便在此处,还有几处兵工作坊,只要何冲将这件事办好,就能让整个南部欠他一个恩情,这批水军和兵工作坊多数都是从当地人中吸纳,只要让南部记住了他这个恩情,以后想从中控制南部并不是什么难事。
司马坤越想越害怕,想从中阻止,又无奈这何冲有鑫通罩着,她们根本奈何不了何冲,三番五次派出的杀手根本连何冲的身都近不了,大大几十号顶级杀手派出去,何冲连佩剑都未出鞘,鑫通的镖师们就已经为他解决一切后患,毕竟鑫通之所以能够在商界纵横无敌手,靠的不仅仅只是那些商业上长袖善舞的掌柜们,同样也有这些身手不凡,在外流血流汗的镖师护卫队们的一份功劳。
正当所有人把注意力都放在何冲身上的时候,静妃院里的掌事宫女被刑察院抓了,罪名是偷盗宫中珍宝。
其实一般这种罪名也不是什么大事,最多让静妃在宫中静闭思过几天,可在在刑察院在静妃院内搜查赃物的时候,发现其中还有数件本该放置在绝珍馆里保管的无上秘宝,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此事一出薛世章就如同猎犬一般,看到猎物紧咬不放,硬是将小小的偷盗罪延伸到对皇帝不敬,对苍雷不敬的高度上,这一顶又一顶的大罪高帽压在静妃头顶上,东天极迫于无奈,只好废除了静妃的妃位,贬为御秀,移居梅心东怨——朱玉阁。
司马仪莫名其妙的失了一个静妃,马上派人去查静妃因为手下犯偷盗罪却无辜连坐的起因,没想到还没来得及去查,真相自己就浮出了水面。
原来是静妃的父亲在容城犯了事,强抢民妇,逼死了一家三口,当地县丞看不过眼,欲秘密上京告御状,接过被静妃父亲安排的人劫杀在半路。
原本此事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却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那莫家军周临将军座下参谋官秦浩告假回乡探望老娘,途经此地,听到那县丞的家属说起此事,侠肝义胆的参谋官眼里哪里容得下此等大逆不道的事情,立即快马加鞭回到军营禀报周临。
这周临刚正不阿,一听到此事,立即让人给管辖容城的节度使安民乐送信举报此事,这容城受豫州管辖,这豫州的节度使乃是薛世章的人,他一得到这个消息就马上上报给薛世章。
薛世章一听,正好借机铲除卢家康这枚眼中钉,这个卢家康掌握这司马坤的经济命脉,司马坤的财源都是由卢家康一手操持,一除掉卢家康,就等于砍断薛世章的重要经济来源。
一通计划后立即回信让豫州节度使接管了此案,与此同时薛世章还安排人封锁了所有的消息,此事燕京的关注力都在何冲身上,司马坤根本没发现与卢家康断了联系。
一切都跟预想中一样,安民乐在容城顺利的定了卢家康的罪,唯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薛世章把消息封锁的严严实实却独独遗漏了传入宫让卢玉婵筹钱疏通一条。
卢玉婵也是慌不择路,竟忘了将此事告知司马仪,才落得司马仪都没反应过来,她的罪名就已经落实了,还被废了妃位。
等司马仪回过头来查原因时,安民乐已了结了此案,正上报朝廷。
这件事本来莫、薛两家都有插手,一传到朝堂上,你一言,我一语,哪还有司马坤插嘴的份,两方人马直接进行语言逼迫,把卢家康的罪给定了,没给司马坤等人作任何申辩的机会。
卢家康的罪定了,薛世章还不愿意善罢甘休,直接又提起了那已经被贬黜的卢玉婵,罪名是卢玉婵知情不报,以权谋私,妄想为卢家康脱罪,形如同罪。
东天极本想为卢玉婵辩解几句,却被薛世章义正言辞的驳了回去,无奈,只能对卢玉婵重判,接过卢家康直系斩首,家当被抄,卢玉婵被剥夺佳丽品阶,判其终生幽禁在青越宫。
瑞华殿
司马仪正在店里大吵大闹,以摔砸东西泄愤,正好筱雪跑了进来。
“娘娘,奴婢有事禀报!”
“出去全都给本宫出去!本宫什么都不想听!!”司马仪被气昏了头,哪还顾得上什么其他事。
“关于薛世景!”筱雪当然也想听从司马仪的命令退出去,不过她觉得这件事如果不让司马仪知道,司马仪会更生气。
“说!”司马仪一听到薛字,马上就停下了手上的摔砸动作。
“奴婢已经查出那杨福的来历,与薛世景有关系,”筱雪也是经过一番训练的人,面对司马仪怒火滔天,仍是镇定自若。
“继续说。”司马仪端坐在大堂上,居高临下的看着筱雪道。
“这杨福归罗志奇管,二罗志奇看似不参与派系之争,暗地里却偷偷的与薛世景相见,奴婢见此事蹊跷,又顺着查了下去,发现宫中许多看似不依附任何派系的人,其实暗地里都与薛世景相交多年,宫中很多消息都是经她们手传到宫外的,”筱雪不温不火的将她查到的线索全部告知司马仪。
“好你个薛家兄弟!竟然里应外合!今日本宫就要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司马仪也不是软柿子,随你们揉捏,筱雪传本宫命令!动用我们手上的所有资源!我要将薛家兄弟在宫中的眼线一个不留!”司马仪将嘴银牙咬得“咯咯”作响,面容狰狞得像是恨不得将薛氏兄弟千刀万剐。
“娘娘,如此兴师动众,怕是会激怒薛氏兄弟,到时候他们还击起来,怕我们也无法全身而退!”筱雪虽也痛恨这薛氏兄弟,却也能明辨出司马仪如此做事,会有不妥。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为了将这两兄弟一网打尽,牺牲几个小小的卒子算什么!本宫要他们死!本宫要他们死!”司马仪瞠目欲裂,一心只想报复这薛氏兄弟,哪还管得了那许多。
“是!”筱雪见劝阻不得,只好按照命令行事。
没过几天,宫里的消息传到了薛世景耳中,薛世景自然也是火冒三丈,这么多风风雨雨都躲过来了,今天却被这司马仪一下子扫除了他好几个眼线,这让他如何不恼,如何不怒。
一气之下,薛世景决定反击,于是乎,薛世景、司马仪这场互相清扫眼线的角力之战中,便如火如荼的拉开了帷幕。
七天后,薛世景突然幡然醒悟,这场消耗战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光是白白消耗了他多年累积下来的积蓄,于是他蛰伏了起来。
这边厢,司马仪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仍然还在孜孜不倦的清除薛世景的眼线,只是发现薛世景忽然就不反抗了,似乎是眼线已经所剩无几,又似乎是故意藏了起来。
可司马仪才管不得那许多,她只把这当做一场胜利,薛世景退缩,那是在示弱。
司马仪得意洋洋之际,楚洛洛找上门来了。
“臣妾见过娘娘,”楚洛洛草草的行了礼,来到司马仪身边。
司马仪见楚洛洛眉头紧锁,知道是要紧事,当即示意让侍从退出殿外。
“娘娘,您近来是否在清除薛世景的眼线?”楚洛洛急不可耐,遂直言相问。
“是啊,”司马仪喜不自胜道。
“娘娘为何不知会我一声?”楚洛洛这场战争打响了十来天,她竟今日才得到消息。
“怎么,本宫做事还要得你允许不成?!”楚洛洛类似责备的话语,让司马仪认为楚洛洛在挑战她权威,令她非常不悦。
“臣妾不敢,”楚洛洛意识到自己言辞有误,立即下跪致歉。
“那你是什么意思?”司马仪怒视了楚洛洛一眼,以示威仪。
“娘娘莫恼,请听臣妾细细道来,”楚洛洛知此事不宜强辩,只好软言相劝。
“说!”见楚洛洛服了软,司马仪便不再计较。
“娘娘为何要与那薛世景斗?”楚洛洛不敢直说司马仪愚蠢只好慢慢引导。
“为了让这薛世景知道,本宫有得是法子让他死!”说到薛世景,司马仪便怒火中烧。
“既然娘娘都说了有得是法子,那又何必急在这一时?”楚洛洛变相的在说司马仪为逞一时之快做了糊涂事。
“你此话怎讲?”司马仪听得出楚洛洛是话中有话,却不能理解楚洛洛的意思。
“您与薛世景斗了个两败俱伤,光让别人看了笑话,捞不到半点好处!”要是她早知道司马仪会如此冲动,一定会不顾一切的阻止,可最气愤的是司马仪根本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完全忘了要知会薛世景,甚至是把她叫过来一起商量。
“谁说没有好处!薛世景对本宫服了软!他们也同样痛失了不少棋子,现在他就像一只缩头乌龟一样,抱着他的惨败独自悲伤呢!”司马仪只要一想到薛世景的败将之相,心中欢愉油然而起。
“他那哪是服软,他那里是看穿了本质,不愿与娘娘您消耗下去!”或许这原本就是别人准备好的圈套,就想看着他们斗个两败俱伤,他们好坐享其成。
“你说得不对!我们是赢了!”司马仪已想到了楚洛洛索要表达的事,但她就是不愿相信。
“我们哪里赢了?与薛世景斗了个你死我活,到头来不仅手头上能用的人没剩几个,还把剩下的人的行踪全暴露了出来!”楚洛洛是恨铁不成钢,摇头惋惜。
经楚洛洛这么一说,司马仪总算认清了本质,震惊的说不出一句话来,眼神中全是懊悔。
“我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司马仪像抓住稻草一般,死死的抓住楚洛洛的臂膀。
“事已至此,眼瞎我们最该做的就是要让那莫承欢吃些亏了,这样才能弥补回来被她算计的那些损失,”楚洛洛恶狠狠的念着莫承欢的名字。
“那该如何做?”司马仪也恨莫承欢,可经过这件事以后,她再不敢轻举妄动。
“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我们先整顿好我们仅剩的人手,不要到时候需要办事的人都找不到。”楚洛洛在等一个何事的时机,莫承欢太聪明,贸然行动只会得不偿失,所以她们需要足够的耐心。
薛世景在家里思来想去,也终于明白了过来,冒险进宫,让薛诗采把楼玉宇叫过去试探。
“楼太医近来忙什么呢?”薛诗采忍着一肚子怒火,假装心平气和的和楼玉宇闲话家常。
“托圣上的宏福最近正忙着帮圣上调理身体,”楼玉宇当然知道薛诗采的目的,只是他也不想明说,他要让薛诗采先开这个口。
“近来就没与莫御秀联系?”薛诗采心想打了一场大胜仗,还不欢呼庆祝一番。
“莫御秀为宫中佳丽,官为宫中御医,若时常见面未免不妥,”楼玉宇觉得既然薛诗采愿意与他打马虎眼,他也不介意和她多费唇舌再说几句。
“楼太医可不要说这种违心话,”薛诗采起身走到楼玉宇身边围着楼玉宇走了一圈:“楼玉宇嘴上说不妥,可实际跑婵心苑跑得比谁都勤快,连人家自己的医者都望尘莫及呢。”
“常宣哪里话,这都是宫中御医,哪分你我他,这莫御秀信任下官是下官的荣幸,正如常宣一般,下官往这梅心苑也跑得勤快啊,那不都是常宣身体多有不适么?”薛诗采想把暗话推到明面上说,可楼玉宇偏要与你暗着来。
“你!”薛诗采被楼玉宇反将一军,很是不快,脸上马上出现了愠怒之意:“联络员,你别以为司马仪那蠢货看不出来,就把所有人都当做傻子,人人都当这些天的事情当做意外,其实这些都是你设计好的对不对!”
楼玉宇很无辜的耸了耸肩道:“这些天都发生了什么让常宣这般动怒?为何下官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他怎么可能没收到,罗志奇等在宫中从事各部掌事多年的老侍官,在短短几天时间,纷纷倒台落马,这么大的事情,就连太医署里平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三位大医官都啧啧称奇,他这么说也纯属是为了激怒薛诗采而已。
“你少给我在这装疯卖傻,你会不知道这事?这事你就是幕后推手!”薛诗采听了楼玉宇想置身事外的话,怒火攻心,瞬间就忘了薛世景交代“切勿动怒”的话。
“常宣莫要诬赖下官,下官可没有这个能力,下官能做的只有为病患治病解患,哪来的本事做其他事,常宣话不可乱说,”楼玉宇面露惶恐,三言两语把薛诗采说的罪名推脱了干净。
“楼玉宇!事到如今,你还把我当做傻子!真当我不敢动你么!”薛诗采看不惯楼玉宇已久,今日好不容易等到薛世景对他也有意见,还不抓住机会给楼玉宇一个下马威。
“常宣要这么说的话,下官也没有办法,常宣已经认定了常宣口中所说的事情与下官有关,那下官再解释也于事无补,既然常宣已经不再信任下官,那下官便与常宣断了这段时间的情谊把,常宣对下官已有怀疑,下官再留在常宣这里也没什么意思,”楼玉宇假意惋惜状。
“我与你没有什么情谊!”薛诗采回到正位上,唯恐避之不及的恼了楼玉宇一眼。
“既然常宣说了,与下官并无情谊,那下官这副能使人怀孕的方子就留给别人吧。”楼玉宇说完转身向门外走去。
“等等!你方才说什么?”薛诗采忙留住楼玉宇。
“下官就把方子留给别人,”楼玉宇故意漏掉了最重要的字眼。
“什么方子?”薛诗采峨眉竖立了起来,疑虑的问道。
“使人怀孕的方子。”
“你真有使人怀孕的方子?下官为何要诓常宣?”
“那你为何不给莫承欢用,要给我?”薛诗采被楼玉宇利用太多次,已经惧怕了这楼玉宇,不敢轻易相信他。
“下官是与莫御秀提过此事,不过御秀说她目标太明显,现在已是别人眼中的一根尖刺,再怀上龙种,怕没把握留住孩子,”楼玉宇后半句说的是千真万确的大实话,不过那不是莫承欢一个人认为,那是他们统一认为。
薛诗采沉默了,她也觉得楼玉宇的话有些道理,但这件事她也不敢一个人决定。
“你让我考虑考虑。”
“下官有得是时间让常宣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