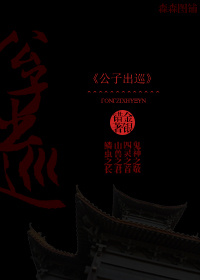“走吧。”
两人沿着小黑指的那条山径小道慢慢走,半山腰温度沁凉,沿边山道的风神出鬼没,疏落的阳光随着风时来时走,云层变幻,远眺是山川,脚下是落叶,树木环绕,山水叮咚,倒是显得十足惬意。
落叶下的路是用石块垒起来的台阶,边缘和缝隙里都布满了青苔,使得能踏足之地更是狭窄,显是此地早已人迹罕至,一如平阳城那样仿佛遭人遗弃。
绕了不多时,期间走过一条笔直的长阶,庙宇的残骸已隐隐约约出现在前方。
这半山腰的位置有些不伦不类,而且小的可怜,在观言看来,此地其实并不适合为神明建造神庙,就算作为墓地风水也仅是尚可,但或许最初天神还没有成为天神的时候,人们只是在这片山中选择了较好的地方为他建陵造墓,并没有人预料到他身死之后的造化。
当观言完全步上台阶,看清楚了全貌后,就更觉得局促,若非神庙被烧毁,此刻他的一脚应该已经跨进了门槛里,前方就是一个大香炉,石碑立于香炉之后,就没有更多的空间了。小到这种程度,反倒让他觉得神庙被烧也没什么不好,不然平时该多拥挤啊,神庙一造,里头连转个身都嫌费劲,也不知最初人们是如何前来祭拜的。
石碑上的字迹也很是模糊,观言盯着一团又一团的痕迹研究了半天,还是什么都没能分辨出来。
应皇天则是连台阶都没有上,显然是不愿上去与观言挤在一块儿。
反观观言,已经撸起袖子动手收拾起来,他跟应皇天说了一声,便开始将烧毁的断梁堆在角落,又将瓦片垒整齐,期间还让小黑帮忙取了水,将石碑擦了一遍。这一通忙完,太阳早已下山,观言朝着石碑拜了拜,念了几句祝辞,这才又沿着石阶回到小黑载他们落地的地方,那儿应皇天正在张罗吃食,让他收拾是万万不能的,但要他烤点儿野味,那几乎是有求必应的。
山野间火光锃亮,没走近就觉得热腾腾的,观言干了一下午的活,倒是不觉得冷,不过一旦停下来不动,夜晚的山风就能冷冽冻人了。烤架上有肉有鱼,在如此荒山野岭丰盛得毫无道理,这一带也不像神庙那儿似的沿着山边,山风要小很多,应皇天又选了一个背风的位置,抬头还能望月,这就地取材附庸风雅的本领仿佛是应皇天与生俱来的本能,每每都让观言叹为观止。应皇天明明就是一个贵公子,和野外这种地方半点都搭不上边,可偏偏就是那么奇怪,只要有他在,观言在哪儿都觉得像是身在重楼里,舒适又坦然,从容又悠闲。
“鱼已经好了,自己拿。”应皇天早就已经吃上了,他无论在哪里,吃东西都慢条斯理的,就算是用手抓着吃,也显得斯文和气,可看起来却是吃得津津有味喷喷香的。
观言也饿了,应皇天烤的鱼总是又脆又嫩,香味扑鼻,他拿起叉在竹签上的一条“呼呼”吹了几下,就迫不及待地吃上了,一边吃一边继续吹,烫到嘴了也不肯罢休。
“今晚好好睡一觉,什么都不必想,说不定奢生还会出现,不用着急。”应皇天给观言斟了酒,递过来道。
这一回这酒又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正如他手中那根叉鱼的长签,这些观言都已经懒得问了,他只管一口将酒喝下,然后长长舒了一口气。
“本来我觉得应该就是的,哪里知道……”观言自觉并未表现出失望来,但他的确在第一眼看见神庙时就感到失望了,只因神庙跟梦中所见的景象完全不同,梦中石碑的方向朝南,他面对石碑时能远眺山下,而神庙却是面向石阶的方向,石碑居中安置在神庙内,却是朝东的。当然最大的不同还在于梦中压根就没有神庙的存在,石碑也因为坟墓被挖掘一空的缘故倒在一旁,唯一相似的恐怕只有一处,那就是梦中的空坟也早被遗弃,虽然不知道坟墓是被谁所盗,可显然这重大的事压根无人追究,梦中他站在空坟前只觉得周遭全是荒芜,神庙的残骸也给了他同样的感觉,这便是梦境和现实唯一相似的地方了。
他将这些感觉也跟应皇天一并说了,然后道:“梦境总归是梦境,会不会只是个提示?我始终觉得应该就在这里,至少在这座山上,当时掌柜提到天神和托梦的时候,我几乎认定那是奢生了,就算现在亲眼见到了神庙,收拾了一通连半点线索都没有找到,我都不能完全将这个猜测否定掉。”
应皇天听后便道:“你注意到没有,我们这一路都是顺着梦境的提示而来,包括这里,看起来是掌柜的梦境,但却合乎我们的寻找轨迹,所以其实我毫不怀疑此地正是你梦中所见的空坟所在,甚至于我另有一个更大胆的推测。”
“什么推测?”观言没想到应皇天会这么说,老实说在没有线索和证据的情况下,仅靠他的梦境就能让应皇天如此确信让观言好奇也惊奇,他连忙问。
“你梦到的是一座空坟,但现在你所见的并不是空坟,那么到底是还是不是呢?”应皇天淡淡一句,让观言瞬间瞪大了眼睛,他张了张嘴巴,却没能说出一句话来。
“况且,你梦到的是空坟,眼下它却还不是空坟,你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观言愣怔,应皇天的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兴许石碑底下是空坟,第二层是梦境若是提示,那么他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把现实变得跟梦境一样,这两层意思皆指向同一个行动,那就是把坟墓打开。
可是,死者为大,挖坟一事前所未有,除了十恶不赦的盗墓者,没有人会去做这样的事,人的坟墓尚且如此,更遑论是神明之墓?
“怎么?不能?还是不应该?或是不敢?害怕?”从应皇天的口中轻描淡写地蹦出一个又一个反问。
观言讷讷,这些他一个都答不了。这事的确不能,也不应该,但要说敢于这样做也不对,这绝不是能逞强逞能的事,唯一能答的“不害怕”也颇为奇怪,既然不害怕,又为何疑虑重重,裹足不前?
但这又是必然的,正所谓事死如生,毁坏他人的坟墓是重罪,如今看来事出有因,那么,这样的事又是能被允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