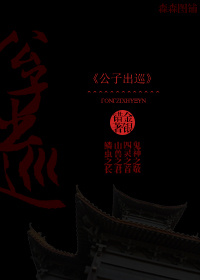腌萝卜是认真的,整整一麻袋的萝卜洗出来,切片,毫不含糊,挚红仔细观察妇人的神情,半点都看不出作假,他愈发疑惑,若妇人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她必定陷入了某种幻觉当中,可是是谁能如此神通广大,能像这样去操控一个人?
一整天安然无事,仿佛他们一直是如此生活的,随着夜晚的到来,挚红准备行动。夜晚翻山越岭其实不现实,尤其是雪山,但夜晚时间很长,又没有外人干扰,趁着夜色探路和试探是挚红白天一直在琢磨的事,他不可能放任夜间就这样流逝,必须要做点什么。
屋外漆黑,好在白天摸熟了去河边的路,挚红依旧沿着这条路走,雪堆砌的路很难掩盖脚步声,无论多轻都仍有“沙沙”声,但挚红并不会天真到觉得自己能在当晚就顺利离开,他总觉得有什么还在等着自己,事情绝不会像今天一整天这样如此简单。
挚红来到河边,沿着下游的方向走。他脑中大概有个方位图,以丹阳为中心,最近的是荆山,再有西边巫山和南边山脉,他在永宁宫昏睡应该只有一夜,要将他连夜安置在山中,除了荆山至多抵达巫山,但若要确保中途不出差错,本来该是荆山最有可能,可是偏偏荆山他比较熟悉,从开始狩猎便出入山中,他直觉这里不是荆山,应该是巫山。
巫山大小山峰无数,连夜上山,必定要选最近的入山口,尤其巫山接壤夔国,那么路线还要绕开夔国,不过不论上山的路线如何,此刻他身在山中,便如同身在迷雾里,就算沿着河水下游一直走,顶多也只是往山下走,而不能确定最终是不是能走出这座山。
挚红自然是打算试试看的,试探归试探,若有机会离开,他不可能放过,只是他的把握不大,偌大的雪山,一整夜的时间显然不够,他也没想过能连夜离开,而是准备先探一探路,通过几晚的时间寻找出确切的方再行动。此刻他一面沿着河边走,一面仔细留意周遭的细节,幸而这夜无雪,河流上方明月当空,照得河面波光粼粼,岸边偶有悉窣响动,可那或许是错觉,毕竟这是隆冬而非夏天的夜晚,动物多半都在冬眠。
河水蜿蜒直下,走不到半个时辰前方就没有了路,水沿着山壁就那样直泻而下,挚红往下张望,而后沿着有路的方向拐了弯,彻底与河水的方向岔开,也不知道这条路会带他去到哪里。
水流声越来越远一直到再也听不见的时候,挚红觉得眼前这条路可能会延伸到很远的地方,他仍然可以往前走,可他不打算冒这个险,挚红转身回头,此际月亮已悄悄绕到了树梢后,挚红粗粗估算,距离他离开小屋应该早就已经超过了一个时辰。
回去的路挚红依然仔细,一路都似是在观察什么,距离天亮还早,他不用匆忙赶回去,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心中忽然升起一股不安,随着越渐接近小屋的方向而逐渐扩大,而后他弄清楚了原因,只因这一路太安静了,他所预想的监视并未出现,他走得那么慢,足够察觉任何一丝细微的动静,然而这一路上却是什么可疑的情形都不曾发生,当挚红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个念头逐渐形成,他觉得对方的监视也许不仅仅是针对他,而或许是那个小屋,小屋里有两个人,他和妇人。
挚红加快了脚步,如果他的直觉是对的,他这边若然无事,那么会出事的或许是妇人。
之前他就一直在奇怪,为什么妇人会心安理得接受一个其他人作为“儿子”,他想过很多种理由,比如被迫被威胁,又或者服用了某种带有幻觉的药物,但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她的自愿的,出于某种理由,比如曾经失去过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应该有他那么大,于是她怀抱着某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前来,仿佛是为了弥补失去的遗憾。
血腥味扑鼻而入,在满是白雪的冷冽之地,这种味道尤为突兀。
挚红的脚步微微一顿,他已经看见了鲜红的血从小屋的门缝处流淌出来,映在皑皑白雪上,看得人触目惊心。
门虚掩着,挚红伸手轻轻推开。
“吱呀”一声,妇人提着油灯匆匆走出来,见是挚红不禁露出了笑容:“你回来啦。”
挚红浑身的血却倏地冷了,只因这妇人压根不是之前的那一个,而此际她的脚下全是血,她却恍若未觉,好像踩在干净的地板上,对他的离开更是觉得平常,如同他本该在这个时候回来。
血还在蜿蜒直流,挚红有一刻只觉得场面荒诞至极,然而这一刻过后,他点点头,对眼前的妇人说:“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醒的?怎么不多睡会儿?”
“醒了就睡不着了,上年纪了。”妇人笑呵呵地说。
“再去睡会儿吧,天还没亮。”挚红说。
“也好,你也休息一下吧,折腾了一晚上了。”
挚红点头,跟着妇人进了屋,他在屋中并没有看见尸体,想来尸体已经被收拾掉了,让他看见血迹不过是用作警告——若再擅自离开,那么这一位妇人的性命也将不保——挚红很难不这么想,但也许对方只是做个样子,之前那位妇人并没有被害而是被带走了,只是无论哪一种,对方都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要他别再轻举妄动。
挚红回到床榻,和衣上榻,他闭上眼睛,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
这件事诡异万分,用一个他人来威胁自己,如何确保有用?若不能确保,对方又为何要用?另外,为什么是“母亲”?意指为何?难到意思是所有危险最终都指向他真正的母亲?若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警告就很严重了。
挚红强迫自己入睡,在这种情况下,睡眠与食物同等重要,这对他来说并不难做到,他从小就接受训练,不知是不是因为毋康病情的缘故,楚王对健康的他就显得格外重视,要不然他也不可能仅在十四岁的年纪就夺得帅印领军出征,然而他的母亲却一丁点都受不了,每次都抱着他直嚷心疼,说完又要埋怨他的父王不像个父王,对自己的孩子过分严厉。这些挚红倒没什么感觉,他觉得身为楚国二公子,强大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从小就敬仰自己的父王,因为他的父王足够强大,强大到一整个楚国都好似在他的庇护之下。
挚红少梦,尤其是对距离天亮已不远的补眠的这一觉来说,理应无梦的他却做了一个梦,梦中他似乎一直在山中打转,风雪大得迷了他的眼,他什么都看不清楚,可偏偏却在大风大雪中看见了点点星火,他眯起眼睛,分辨不出来那究竟是灯火还是无数的火把,就在这时,梦醒了,挚红睁开眼睛。
“你醒了,昨夜睡得好吗?”
一模一样的问话,同样的熟络和亲切,却出自不同的妇人。
挚红向门边望去,地上的血迹被拖干净了,若非能看见依稀的痕迹,真的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