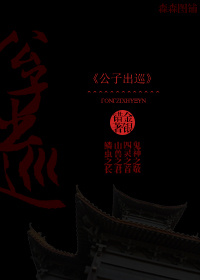一瞬的光亮划过,伴随一声惊雷,刹那间响彻夜空,随即大雨倾盆,乌黑的天空中好似有什么在那里不断暴动,掀起大风大雨,无法平静。
重楼外高悬的灯笼在风雨中飘摇,烛火明灭,偏是不熄。
扶风就是在这样一个雨夜匆匆来到了重楼。
应皇天未卜先知似的在小楼里等着他,丝毫不以他到来的时间古怪又不合时宜为意,他眉宇间的神情甚至有几分凝重,这是鲜少能见的,他的指尖轻点着几面,看似凝望窗外夜色,又像是在倾听磅礴雨声,却又无一留在心间,茶水雾气虚化了他沉吟又精致的眉眼,扶风披着夜色和雨水,湿漉漉地进了重楼的门。
门簪落下,隔绝了外头的风雨,扶风一进门就对应皇天说:“应公子,二公子不好了。”
他神色焦急,语气凝重,说出来的这句话每一个字都带着不祥的意味。
应皇天仿佛早有预料,只是微一点头,便让香兰先带扶风去洗浴,香兰安置好了扶风,出来重新上了一壶茶,顺带将楼里的水渍收拾干净,片刻的工夫,扶风就出来了,他换上了干衣服,喝了一口刚为他准备的茶水,在应皇天面前坐了下来。
“把这段时日以来的情况跟我说一遍。”应皇天道。
“好。”扶风来之前早就将来龙去脉理过好几遍,因而开口便道:“三个月前,也就是在年初祭祀后一次狩猎宴上,二公子被一头野豹抓伤,这本不是严重的伤势,很快就治好了,然而在那之后,二公子就变得不对劲起来,他在熟睡后浑然不知的状态下离开过寝宫,醒来时满身血迹,但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却毫无印象,为此,二公子安排侍卫守夜,不过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第二天我们就发现侍卫已死,而且是一击毙命,又毫无打斗的痕迹,二公子醒后查看侍卫的情况确认了是他自己下的手,据二公子自己分析是出于一种本能,应该是不欲被他人跟踪,他觉得他当时的情况既认不出侍卫,更觉得自己身在敌营,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来,如若不然,理应有打斗的痕迹才对。”扶风顿了顿又道:“自始至终二公子都记不得自己曾经去过哪里,因为每次醒来他都已经回到寝宫,只是身上总是血迹斑斑,而且带着伤,好似经历过一场生死决斗,浑身疲惫不堪,我们秘密找了大夫,也去过巫宗府,后来二公子便决定将他自己囚禁起来,然而在三天前,二公子一睡下去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应皇天听后沉默了好半晌,才道:“他将自己囚禁后情形如何?”
扶风摇头道:“不好,二公子到了晚上就横冲直撞试图离开,一开始我们只是用绳索将他绑起来,后来……”他像是不忍说出口似的,好一会儿才道:“如今囚禁二公子的地方十分牢固,他就是弄伤自己也无法逃脱……”
“轰隆隆”,雷声不绝于耳,直震得扶风心头发慌,他说着忍不住问应皇天:“应公子,你说二公子他会不会……”
应皇天淡然道:“生死有命,我先去看一看,若能救,我不会不救。”
闻言,扶风神色总算松了松,他觉得这世上若有人能救回二公子,那么就只有这一人,如若连他都救不了,那便也只能认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