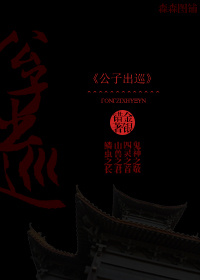“公子,你还没喝药?”香兰走出来催促道,“快点把药喝下去,然后躺到床上休息,知道吗?”
“啰嗦。【】”应皇天说着,眉头深蹙,却端起药碗将里面的药汁一饮而尽,再用衣袖拭掉唇上药渍,一手按席缓缓起身,可不知为何,观言总觉得他的行动微有一丝滞碍,却又看不出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没什么事,我要休息了,观大人要留要走,请自便。”应皇天穿过屏风之前,对观言如此道。
观言看着他消失在屏风之后,听见他上楼的脚步声,直到重楼又再度恢复安静之后,他转过视线望向那只空碗,默默无言。
过了不知多久,楼上似又有人一步一步走下来,随即,观言便看见香兰抱着一只脸盆再度出现,香兰看见他亦是一怔,“观大人,公子已经休息,若还有什么事,请改日再来吧。”
观言不语,却将视线望向她手中的脸盆,只见里面满满的都是带有血渍的纱布,他一怔问道,“是谁受伤了?他吗?”
“香兰以为重楼之事跟观大人再无瓜葛,观大人又何必如此关心?”香兰冷冷地道。
“我……”她的话令观言哑口无言,只说了一个字就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
香兰也不等他说话,而是抱着脸盆去到重楼外,她走到长廊的台阶上,点了火扔进脸盆里,欲将里面带血的纱布烧掉。
观言这样看着,越来越不放心,蓦地便转身跑到屏风后,他看见楼梯便拾阶而上,事实上他从未到过二楼,但这时他顾不上其他,就听二楼其中一间房里传来应皇天低哑的声音,“香兰——”
然而他的声音却静止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只因他抬起头看见了一脸担忧的观言正扶着门框站在外面。
观言也是震惊万分,应皇天的右肩裹着纱布,血迹正逐渐从里面一点一点渗透出来,虽说好像刚换过,但已然殷红一片,而他似乎正打算将右边的衣服重新穿回去,却因为受伤的缘故并不顺利,因而听见脚步声时才会出声低唤香兰,却并没想到出现的是自己。
“我来帮你。”观言想都没想就跑上去,应皇天见既然被他发现便懒得再多言,也没力气阻止,观言这才明白过来刚才自己的疑惑从何而来,难怪刚才他看见应皇天的动作有些缓慢,虽然此时他还不知道他的肩膀是怎么受伤的,可当他走近之后便看见从锁骨下一直到后背的肩胛骨都透着血迹,恐怕伤得相当严重,也难怪他一咳嗽就牵痛伤口,现在的他一身冷汗,又面无血色,显然是方才换纱布耗费了太多的精力所致。
观言轻轻地将衣服一件一件帮应皇天套回去,再理顺前襟,才发现他穿得果然够多的,可身上的皮肤却在发烫,看起来烧得不轻,也难怪会畏冷。
他真没想到自己一个月不来应皇天就把自己搞成这副糟糕的模样,到底这一个月间发生过什么事,还有大公主交代他说应皇天曾劫回的那名患病的侍从,他人又在哪里?
“好了。”观言说着,退开几步,“那……你先休息吧,我不打扰你了。”
“等一下。”应皇天终于开口。
“嗯?”观言回过头看他。
“你今日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应皇天再问。
观言想了想,还是没回答,却问,“你能否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会伤成这样?”
“咳,我怎么会受伤的,与你无关。”
“我知道了,我不会再问。”观言虽是这么说,却依然难掩受伤的表情。
应皇天看着他片刻,忽地道,“大宗伯说过,我太过不祥,你现在也亲眼看见了,我劝你还是不要接近我比较好。”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不是因为这样才不敢来见你。”观言猛力地摇头道,“我是因为,是因为害怕连累到我义父,因为我亦是一名巫师,而那召唤鬼神的传闻,就算是这样又如何?你从没做过一件不好的事,那些不了解你的人只会胡乱猜测,不负责任乱传,他们看见的只是表面,又凭什么说你是不祥之子,是你告诉我看事物不能只看他们的表面,可我的义父又是大宗伯,他要做出表率,而我……”
应皇天忽地打断他,问,“你可知晓因为我的不祥,以至于我的母亲将刚出生的我扔到野外?”
“呃?”观言闻言一怔,想起大公主说的对不起他的事,兴许指的就是这一件……
他来不及问,应皇天又道,“你又知不知道我出生那日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
观言摇头。
“你可知是我害死了我的父亲?”
观言只能摇头。
应皇天低低的笑,低声地咳,“咳咳,呵……你什么都不知道,竟说我不是不祥之子……”
这回轮到观言打断他,他不喜欢看到应皇天这副样子,也许是因为生病的缘故,他在一贯倔强的人身上看见了几分认命,几分自暴自弃,他不喜欢看他这样,一点也不,因此他大声道,“你不是,我知道你不是!”
应皇天闻言一愣,怔怔地看着他,过了好一会儿,才静静地开口,“你说我不是?你凭什么这么说呢?你有多大的把握能这样说?”
一句话,把观言问住了,他看着应皇天怔怔无言,半晌,他才一字一句地道,“你不信我,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会证明给所有人看。”
应皇天却因他这句话笑了,笑容里有一种惯有的傲慢和不屑,“随便你,我何必在乎那些人怎么看我?”
“我在乎!”观言不肯认输,他也一样倔强,而且倔强起来的劲就像是一头牛一样怎么拽都拽不回来,他大声说出那三个字后,语调却又低了几分,目不转睛注视应皇天道,“只因我不想像现在这样,无缘无故失去你这个朋友。”
应皇天因他的话静默了好一会儿,最终蹙着眉别过脸去寥寥地道,“我知道了,你不用再三强调。”他说着拉起棉被便背朝观言躺下,又轻咳了几声。
观言一怔,他分明看见方才应皇天别过脸时有一抹微微不自在的神情浮现,相识已久,观言从未见他流露出这样的表情,虽然只有一瞬间,也可能是他的错觉,但这已经使得他的心情不知为何稍稍放松下来,总觉得他们俩已不像刚才那样既尴尬又好似一触即发,这时观言见应皇天睡下,便轻轻退了出去,走下楼梯。
香兰见他从楼梯上下来,便知他已经得知自家公子受伤的事,果然观言第一句话就关心地问她说,“应公子究竟是如何受伤的?”
“你真的想知道?”香兰看着他问。
观言点头。
香兰深深蹙起眉,依然板着脸,但她毕竟愿意告诉观言,就听她叹一口气道,“其实每年一到这个时节公子就会这样,但具体发生了什么事香兰也不清楚。”
观言听得迷糊,问,“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时节他会变成这样?他肩膀上的伤难道也跟时节有关?”
香兰摇摇头道,“香兰指的时节,是狩猎的季节,每年在这段期间,公子就会离开重楼几日,还记得香兰来到重楼的第一年,公子离开后便带病而归,第二年依然如此,因此今年香兰便偷偷跟踪他,终于知道他是去了哪里。”
“究竟是哪里?”观言再问。
香兰迟疑片刻,回答观言,可这个答案却让观言冷不丁一惊。
只因香兰说的竟是,“让公子受伤的地方,是祀林苑。”
“祀林苑?”
香兰点头,便将她所知道的情形告知观言,“要不是大宗伯来访,香兰本想请观公子一起跟踪公子前去,但自从那日大宗伯来访之后公子就让香兰绝对不能再来打扰观公子,因为观公子是巫师,不能跟重楼之人为伍,因此香兰只能独自前去,谁料公子在祀林苑外就发现了我的踪迹,看穿了我的意图,把我赶了回来,我担心不已,便找了途林前去接应,结果公子回来就是这副样子,哦,不对,比你现在看到的还要糟糕好几倍,因为那支箭有毒,伤口简直惨不忍睹。”香兰说的时候表情也是一样不忍和纠结,似乎又想起了那日所见到的糟糕的伤口。
观言这才明白香兰因何会对自己如此耿耿于怀,实际上他听后也已不觉暗自自责,若不是他这近一个月来的不闻不问,说不定就能提早阻止应皇天前去。
但究竟为什么会是祀林苑,观言完全想不通,而且方才大公主说话时的感觉似是并不知道应皇天受伤的事,否则又岂会无动于衷,提也不提?而且祀林苑之中究竟藏有什么秘密,以至于吸引应皇天每年前去?
想到这里,观言忽然问,“应公子回重楼的时候,是否还带回来一个人?”
香兰却是一怔,疑惑地道,“此事观公子如何知晓?”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