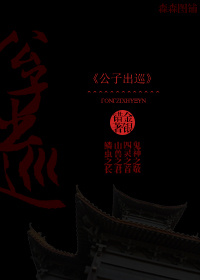夜色沉得如同深渊,无止无尽,挚红整个人都陷在风雪里,寒冷一点一点蚕食他的体力,饥饿如影随形,他只有不断地让自己往前走,才不至于被冻僵,可就算意志力再强大,体力也在不断流失,更何况不久之前他才昏迷过,挚红强撑着走了整整一夜,当天色见亮,他微仰头,见到些微的日光从树梢的缝隙中透进来,心头稍有放松,可是只这一个细微的动作和一丁点的松懈,他就觉得头晕目眩,整个人摇摇欲坠,下一刻身体像是断了弦一样软倒在地,疲惫瞬间席卷而来,他试图让自己重新站起来,意识却愈发恍惚,最终陷入了沉沉的黑暗之中,不省人事。
挚红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个梦,梦中出现一个村庄,那个村庄人丁兴旺,家家和美,每到既定的日子,村民们就携家带口上山祭祀,那山上似有一位厉害的神明,村民们纷纷献上祭品,虔诚地向神明磕头跪拜,口中念念有词。
神明的存在逐渐被村外的人们所知,陆续有外来者寻访上山,一样磕头跪拜,每个人脸上都似是怀有期待,也有不安,然而画面一转,那些人皆怀抱着婴儿再度上山,这一回他们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喜气,一看就知道他们的愿望实现了,纷纷上山来还愿。他们替神明修建庙宇,同时也将这位神明的名声传播到了更遥远的所在。
而后,更多的人慕名拜访,又得愿而归,神明的庙宇终日香火兴旺,信徒们络绎不绝,连带着山脚下那个小村庄也红火起来,原本简陋的村落建起了四四方方的大院,为了迎接四方前来朝拜的信徒,他们铺起了长长的青石板路,整个村庄焕然一新,但不知不觉间,村民们开始以侍神者自居,言行举止也逐渐傲慢起来,他们越渐贪婪,甚至越渐自大起来。
神明的名声自然也传到了南方,南方荒蛮,方国众多,大小不一,有些方国还不比眼前这个小小的村庄富有,他们一样想要上山拜神,却被村民们苛待和阻拦,终于村民们的做法惹来了方国的怒火,那场滔天大火将所有风光都烧成了灰,村庄一夕没落,村民们本还寄希望于山上的神明,可惜他们的傲慢和自大早一步将神明的名声毁坏,被他们苛待的方国将村民们丑恶的嘴脸传了个遍,都说神明必定是假的,否则那些村民们为何阻拦?一传十十传百,尽管神明的拥护者为神明辩驳,可惜挡不住有心人恶意传播,久而久之,神明的名声沉寂下来,再也没有什么信徒,那个曾经人头攒动香火不熄的华丽庙宇,也日渐衰败下去,再不复往日盛况。
-------------------------------------------------------------------
“醒了,他醒了!”一个略带低沉的嗓音传入挚红的耳中,他缓缓睁开眼,见到了两张忧心忡忡的脸,这两张脸一入眼,挚红就觉得自己的心猛地一跳,他闭上眼睛,凝了凝神,睁眼再看。
挚红深知自己的长相,他的父王英武非凡,他的母亲二夫人纤柔婉约,而自己也算是五官端正,隐约是有父王的影子,可是他乍然见到面前的二人,却冷不丁怔住,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像,也不知道是五官的哪一部分还是揉合了全部之后的感觉,总归这两人自有相似之处,而与自己的父王甚至是他自己都有几分相似,挚红眼皮直跳,总不至于自己的父王其实另有兄弟流落在外?
念头一闪而过,眼前二人一男一女看似是一对夫妻,他们凑过来时相互靠得很近,仿佛不分彼此,他们的担忧也不外露,见他醒来只是小小松了一口气,就听那男的道:“醒来就没事了,多喝水多休息多吃一点就能恢复过来。”
女的听后放下心来,却是问挚红:“小兄弟是一个人上山的吗?我们是在山里发现你的,怎么在这样的天气里上山来啊?”她问话的语气十分温柔,让人生不出丁点不回答的意愿,挚红没有忽略这种怪异的感觉,但他到底是被搭救的一方,便略去许多关键的情况答:“不止我一个,我和同伴们走散了,这种天气实在不该上山,只是我们急着找一个人。”
“别光顾着问,先让他吃点东西。”男的推了推女的说。
“啊,是,我去把吃的端过来。”女的连忙说。
“我起来吃。”挚红撑着床沿坐起来,从小的礼仪和教养使得他没有在床榻上吃东西的习惯,但他发现自己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饶是如此,他还是让自己坐起来,没再让自己跌回去。
男人立时看了出来,连忙对挚红说:“别急,你坐着别动,我们把小几搭起来,你就在这儿先吃一点,蓄点力气再说。”
挚红知道自己的情况,没再拒绝,眼看着男人搭起小几,女人将茶水和饭菜一一摆开,那是十分简单的菜色,却非常清淡可口,先前他在小屋里分别尝过两位妇人的手艺,都不似这般,那二人只给他普通村妇的感觉,但这次不同,食物里透着几分用心,他还记得第一位妇人切的萝卜块,若说他曾经想找出几分装模做样的痕迹的话,那么现在仿佛能从那些粗糙的萝卜块中看出几分端倪,不过也许是自己过分挑剔了,萝卜块切得粗糙显然不能代表对方不够用心。
挚红的体力在陌生男女的照料下逐渐恢复了过来,如今他们也不能算陌生了,他得知了他们的名字,男的姓傅,本身就是大夫,女的正是他的妻子,他们是最近来到这座山下的小小村落里的。
挚红第二天就走遍了小小的山村,这里位于雪山下,这显然不是自己走下来的,而是傅大夫上山发现昏迷的他之后把他给救下来的。
山村极小,没几户人家,村子里发生一点小事大家都能知道,村民们也很是质朴,对挚红的到来纷纷表示欢迎,没用多少工夫挚红就从村民口中了解到了傅氏夫妇的一些情况,他们成婚多年,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出生不久就被人抱走了,两人多年来一直到处找寻,却屡次失望,但若那孩子还活着,差不多就是挚红这样的年纪,说到这里的时候,村民看向挚红,皆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挚红看得分明,这多半就是他们也觉得自己与傅氏夫妇生得相像的缘故,就好像自己是那对夫妇失落多年的孩子。
但若说傅氏夫妇觉得救了他是冥冥之中上天注定,那么对挚红而言,便是有人刻意安排,让他与傅氏夫妇相见。
从他被绑到山中小屋开始,这件事就一直围绕着母亲和孩子,要不是挚红万分确信自己是父王和二夫人亲生的,到了此刻他也要开始产生怀疑了,但对方一直针对这一点,或许真的有这个目的,又或许对方不知为何会以为他的身世有问题,才要像这样千方百计来提醒于他?挚红按兵不动,他与村民聊了半天,傅氏夫妇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必然也想得到村民们会如何说,但他们却在挚红回来后回避了这个话题,仿佛是想认一认又怕最终是错认,这从他们待他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强忍激动,又有几分小心翼翼,不刻意嘘寒问暖,但尽可能将一切都安排妥帖,怀抱着想将天底下最好的东西都给他的心情,这种心情挚红在自己母亲的身上感受过,所以一点都不觉得陌生,但他也绝不可能接受另外一份同样的心情,只是傅氏夫妇与先前的两名妇人又有截然的不同,他对于他们失去孩子一事有些于心不忍,衷心希望他们能将孩子找回来,至于像后者那样自然将他认作孩子的情况,他可以忽略的彻底,丝毫也不会放在心上。
他并没有受伤,体力恢复后按理就能提出离开,可是一来幕后之人毫无线索,二来傅氏夫妇的来历到底令他好奇,三来他也想确定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没有人会把“幕后者”三个字挂在脑门上,那么便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一条。挚红的防备心很重,越是觉得面容相似越不会把这一点简单放过,那些人把他送来这里,不就是要他深挖这一点吗?挚红觉得自己没必要像他们一样躲闪,索性就开门见山:“前几日无意中听说了一件事,若是冒犯了还请傅大夫和傅夫人多见谅。”
话开了头,自然就有了后文,傅氏夫妇必然也是等着这一刻的,但他们失去孩子的悲伤早已经因为过去太多年而沉淀下来,只是面对挚红的时候仍是难掩遗憾和伤怀,若眼前的青年真的是他们的骨肉,那么他们也失去了最能同他亲近的时期,如若不是,那么又将会是一场空。
“他是我们好不容易求来的,却没护好,把他弄丢了。”傅夫人的话中带着浓浓的自责,傅大夫抓住了她的手,拍了拍接下了她的话,问挚红:“你听说过武罗神吗?”
这话要放在半个月之前问挚红,他必然是摇头,可是扶风上山后就跟他说了武罗神的来历,而此刻傅大夫的话让挚红蓦然间联系上了之前的梦境,顿时明白过来傅夫人刚才说的“求来的”是什么意思,他没有立时回答傅大夫的话,而是反问了他一句:“你们见到了那武罗神了吗?”
傅氏夫妇两人点头,又摇头,傅夫人说:“武罗神并未曾见到,但我们去他那儿求子,愿望实现了,却在前去还愿之时把孩子弄丢了。”话说得实在凄然,泪水也是一下子涌了出来,看起来不像是装的。
傅大夫叹息一声,那段过往已然久远,却仍然刻骨铭心:“我们成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听说武罗神是送子神,便去碰碰运气,没想到真的灵验了,她在回家不到半年内就怀上了,我们简直欣喜若狂,都觉得等孩子出世后一定要去还愿才行,我们这样想,也这样做了,孩子出世不到一年,我们就带着他跋山涉水重新去到武罗神所在的那座山的山脚下,那时武罗神已经非常有名了,来往求子和还愿的人很多,当地的人们说怕那么多人一拥而上打扰了山神,就安排外来想要上山的客人分批上山,我们被排在了三日后,然而谁都没想到就在这短短的三日内村庄出了事,那时一片混乱,我们的孩子就在那场混乱中丢失了,再也没能找回来。”
挚红有些吃惊,傅大夫的话和他的梦境如出一辙,但他其实极少做梦,而且就算做了多半都记不得内容,这次不仅做了梦,还如此清晰甚至似是带有某种程度的预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没有让吃惊表现在脸上,只是再问:“能说一下当时的细节吗?”
傅大夫点头,当时的场面尽管混乱异常,可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那些细节他早就回忆了不下数百遍,他从抵达那个村庄开始说起:“我们带着孩子上路非常不方便,为此特地租了一辆马车,那日跟我们一同抵达村庄的还有一队车马,其实在半路上我们还遇到过,当时不知道目的地是一样的,结果到了山脚下,发现原来都是来找武罗神的,不一样的是我们为的是还愿,对方是求子。”
“那是位品貌端庄的夫人,中途遇上时她就表现出对孩子的喜爱,我们的孩子还让她抱过,后来到了山脚下再一次遇上,她非常热情地邀请我们住到她的隔壁,她也要排队等上山,一样是等,我们住哪里都一样,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于是就答应了下来。”
“等待的过程并不无聊,除了那位夫人经常会邀我们出门之外,村庄里的村民们也很热情,他们用来招待我们的饭菜都十分可口,就是这期间有人来闹事,说是这里的村民不让他们上山,但村民们说那么多人总该有个先来后到,总之最后那些人被赶走了,但听说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前来闹事了。”
“之后人心惶惶的,似乎只有当地的村民们把这件事看得很平常,外来的客人都有些不安,总觉得那些闹事的人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可是来都来了,总不至于要为了这点不安就不上山,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无论是求子还是还愿,都是很重要的事,必须要贯彻到底,可是没想到……一念之差,当时我们真的讨论过要先离开的,若真的那样做了就好,那我们的孩子就不会弄丢了……”
傅大夫说到这里长叹一声,无限的悔意和深深的无力感自叹息声中传了出来,好长一阵他才再度开口:“就在最后那天,我们收拾妥当准备上山还愿,下山就离开,马车也都找来了,没想到我们才刚一踏出宅院,凌乱的脚步声传来,有人在外头嚷着‘起火了’,也有人大叫着‘是他们’,场面一片混乱,我们也顾不得上山了,当下决定立刻离开,车夫刚帮我们搬了行李,我们追上车夫上了马车,大火已经从村尾烧了起来,从我们的位置能看见不断往上冒的浓烟,和我们一样逃离的客人很多,还有人冲上了我们的马车,我们没办法赶人下车,只好将孩子看紧了,谁知马车还没出村庄,忽然狠狠颠了一下,我们都吓了一跳,外面全是呼喊声,马车也被人推的不断摇晃,简直像是快要散架一样,刚才上了马车的人见状不对又迅速下了车,我也不得不下车查看情况,外头的情况十分糟糕,车夫受伤摔在了马下,我把车夫送上车,准备自己驾车,但那马儿一点也不听话,就在这时,前方有一辆马车停了下来,正是那位夫人的车驾,她拉开车帘说她的车子还能坐人,让我们赶紧上车。”
“于是我又去扶车夫,同时让妻儿一并下车,我们两辆马车相隔虽说不远,但这时烟雾大了起来,孩子又一直在哭,她哄着儿子,我扶着车夫拉着他们娘俩,短短一路走得十分艰难。夫人那边也很焦急,她索性下车来帮忙,就在这时有人忽然窜了出来,刚巧撞到了我的妻子,我见她整个人往前冲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夫人就在她跟前,她帮忙抱着孩子,顺便拉住我的妻子,我看着她们上了车总算放下心来,哪知又有几个人窜出来挡了我的路,还有人要抢马车,我只能让夫人的马车赶紧走。”傅大夫像是想起了什么,低头将脸埋进手掌,傅夫人也是一脸哀戚,她抬手轻抚自己丈夫的后背,对挚红说:“接下来还是我来说吧,不过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马车的确送我们离开了村庄,我很担心他,可孩子也要紧,只是没多久我们的马车也出了事,我只记得翻车之前听到夫人的惊呼,我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不能让他受半点伤害,可是当我醒来后,孩子就不见了,那个地方只有我和夫人,她也跟我一样昏了过去,马车和其他人都不见了,我心慌异常,孩子不见了我觉得天都要塌了,就一直找一直找。”
傅大夫振作了片刻,才又说话:“我好不容易脱困带着车夫追上马车,却发现马车翻在了半路上,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只好先把车夫放在原地去找人,这一找就是一整天,可是当我找到她们的时候,也知道了噩耗,当天我们还是返回了村庄,想找找线索,可惜村庄如同经历了一场浩劫,谁也没留意那些趁乱离开的马车,而前来闹事的人早就逃之夭夭,我们想过孩子早就被人抱走了,也不会回到村子里,但我们怎么能死心呢,于是一问再问,想知道那几日所有前来求子的人到底都有哪些人,说不定就是那些想要孩子想得厉害的人袭击了她们的马车抱走了孩子,自那之后,我们两人一路走一路找,到今日已经足足十六年,却依然没有半点下落。”
傅大夫的话说完之后三人好一阵沉默,挚红等他们的情绪有所缓和之后,才问了一句:“那位夫人,你们去找过吗?”
傅夫人在挚红这句问话之后瞬间抬起眸:“你是不是怀疑她?其实谁都有可能,毕竟那里都是前来求子的人,可是我事后总会想起那夫人跟我们套近乎和她看孩子的眼神,说不定是她临时起意安排的马车被撞,当时她跟我一起所以我没怀疑,可是后来我不断回想,总觉得只有她最有可能将孩子抱走,因为那里除了她之外车夫和她的下人都不在了,他们能去哪里?为什么会消失?我无数次想过,可是当时我们将夫人送到城里就分开了,她留下的地址我们曾去拜访过,也没能见到人,据说回来不久后就因为家里的事又搬走了。”
挚红基本能从他们说的情况中确定那夫人一定有问题,只是那批去到村子里闹事的人会不会也是受人指使就不能确定了,毕竟眼前这对夫妇上山还愿对那个村庄来说是个寻常事,但话都说到这份上,挚红又问:“当时去还愿的多,还是求子的多?还愿的都抱了孩子吗?”
这些细节傅氏夫妇如数家珍:“求子的多,还愿的还有三对夫妇,我们都打过招呼,也互相夸过他们的孩子。”
“后来有找过他们吗?”
“没有,我们手上有一份好不容易凑得的名单,是当日的住客们的,但其实没有什么用,因为一来名单不全,二来这些人都只登记了姓名,并没有留下能供我们寻找他们下落的讯息。”
挚红陷入沉思,好半晌,他开口说:“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在我离开的时候把名单誊给我一份,但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十六年,至于我,我的身世毋庸置疑,请不必怀疑。”
他的字句有些铿锵,听得傅氏夫妇心里皆是一震,便心照不宣地说到了这里,有些事必须是双方面的,就算眼前这个孩子真的就是他们弄丢的那个,只要对方不愿意,他们也很难以其父母自居,更何况他们直觉这个孩子来历不凡,这从他的举止和言谈间就能看得出来,至于他为何会流落雪山,他若不肯说,他们是没立场问的。
挚红这时却有一种预感,他觉得谜底应该快要揭晓了,他被人安排与傅氏夫妇见面,是果,因则在永宁宫里,那位与傅氏夫妇相遇的夫人,直指自己的母亲,如果他猜得不错,那么接下来幕后的人必然是要让他进一步认识这一个事实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