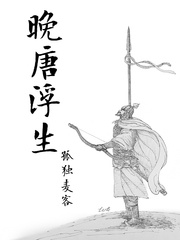西北风呼呼劲吹,几乎要将旗杆折断。
除少数人留守营地,看守马匹、辎重之外,铁骑军大部分人都上马,快速机动到某处,挥汗如雨地忙活着。
还有一些被他们抓到的百姓也动员了起来,忙个不停。
与此同时,还有近千骑在汴军周围游弋着,时不时冒险靠近,千方百计迟滞汴军的行军虚度,虽然收效甚微。
折嗣裕算了算时间,今晚汴军多半要在那个堡寨内休息一晚。然后再行军,差不多明日午时可以抵达预设的攻击地点。
希望明天天气不会有所变化!
邵树德是第二天上午收到折嗣裕传来的加急消息的。
他让人模拟了一下形势,然后沉默不语,仿佛看到了岐沟关之战曹彬被耶律休哥的骑兵围困的场景。
当时曹彬用运粮车充当外围屏障,耶律休哥攻了一下,死伤不轻,于是转入对峙。
按理说,曹彬有从雄州刚带过来的粮草、器械,一时半会辽军也拿他们没办法,不是正好牵制辽军骑兵,给其他两路大军创造机会么?
但曹彬的应对是,深夜打开车障,带人逃跑……
就这战斗意志,被成德骑兵围困的李克用能吊打你十八条街。
这一仗,宋军死万人。
曹彬带残部溃逃后,辽军又追来,其部望风自溃。
李克用也不是没在成德、幽州面前败过,但他总能击退追击的骑兵,从容收拾败局,不至于伤筋动骨。
都是步兵为主,为何差距这么大?
或许,汴梁禁军从朱温建立起开始,到北宋初年,过去了差不多快七八十年了,参照神策军的堕落曲线,也差不多就是这种水平了。可能因为历战事较多,比神策军堕落得慢一些,但存在了数十年的军队,暮气沉沉是难免的。
“给折军使传话,我静候佳音。此战若能大破汴军,当记头功。”邵树德说完后,便出了大营,查看起刚攻下的硖石堡。
这边都是小场面,以精锐步军打张全义的县镇兵、屯田兵,没有什么大的悬念。可能就新安县难打一些,张全义居然破天荒地修缮了那座城池,这么重视“函谷关”吗?
郑州、洛阳大驿道上,车马众多,最先出发的刘捍所部头大无比。
夏军骑兵与他们所遇到的朱瑾、罗弘信的骑兵不太一样。
他们不硬来。
朱瑾骑将出身,最开始总是用精锐骑兵硬冲有辎重车辆保护的步兵,死伤惨重。
吃了几次亏后,开始袭扰粮道,还是没有什么效果。
到最后,可能是人变得狂乱了,今年居然用骑兵硬冲步兵大阵,妄想赌一把,最后全军覆没,狼狈逃窜。
曾经拥有五千以上精锐骑兵的泰宁军,降的降,死的死,已不足为虑。
“刘将军,夏贼是否已放弃袭扰?”随军要籍朱友让看着散在远处的夏军游骑,问道。
“朱随使,夏军未必已放弃,说不定在哪里等着咱们。然我军昨晚休整了一夜,气力充足,士气高昂,不惧夏贼。”朱友让本是汴州豪商,被东平郡王收为义子,如今充当随军要籍,其实是有几分监军味道在内的,他也不敢过分得罪。
刘捍,与杨彦洪一样,都是宣武旧军将校。
杨彦洪统宣武骑军,位高权重。不过也正是因为位置太高了,东平郡王又很眼热他手里的骑兵,于是拉拢他手底下的李思安等人,导致慢慢被边缘化。
但旧军将领也不可能完全不用。
大伙都是世代将校家庭,传承很多,本事还是有的。
不用杨彦洪,李思安得用,不然骑将人才够吗?单靠葛从周、霍存、谢彦章这些巢军骑将够吗?
刘捍现在是左右保胜军都指挥使,俗称都头是也。
带着四千人从郑州出发,充作大军先锋,入援洛阳。
只是没想到,夏军骑兵竟然已活动到这片区域了,看来新安县以西已经彻底糜烂,搞不好夏军主力已进抵新安城下,要围攻这座城池了。
风越吹越大,刺啦一声,一杆旗幡当场折断。
看见的人面有惊容,朱友让也吓得叫出了声。
“沧——”刘捍抽出了横刀,环视左右,道:“西风劲吹,此天时也,何乱耶?”
他让人将断掉的旗幡收起来,又换了一根新的上去。
“不许停,继续走!夏贼难不成还能直冲我大车?”刘捍死死盯着众人,道:“血里火了都走了那么多遭了,杀的贼兵两只手都数不过来,还怕这些?只要将士齐心,便是这天也能捅个窟窿出来。”
众人闻言都笑了,士气有所恢复。
南征北战这么多年,风里雨里,血里火里,杀了个遍。区区夏贼,若敢冲过来,便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终日琢磨的杀人的手艺。
“夏贼若来,某手中这把长槊定痛饮其血,一槊一个。”
“若夏贼来得多了,你待如何?”
“那还不简单?一枪俩。”
“哈哈。”
有几人调节起了气氛,众人士气再度提高。
这就是部队里经历血与火淬炼的老兵多的好处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也不是很怕死,敢打敢拼,对于战争的帮助相当大。
车队继续前行。
有斥候壮着胆子前出,不过很快被压了回来。
众人也不在意,习惯了,一点不影响。
唯一让人不满的,或许就是这风沙有些大,让人很是烦躁。拉车的役畜也有些焦躁不安,不是很听使唤了。
又往前走了一小段,风沙越来越大了。灰蒙蒙的天际边,隐隐传来马蹄声。
“牟!”一头牛烦躁地发起狂来,驭手控制不住,粮车被拉得歪歪斜斜,哐当做响。
“不好!”刘捍大步跨上一辆驴车,沙尘铺天盖地,虽不至于眼睛都睁不开,但也极为难受。
河南哪来的风沙?
马蹄声越来越急。
“哐啷”一辆牛车冲出队列,下到了田野中,然后侧翻在地。
大部分役畜都焦躁起来,它们并不适应这样的环境。
其实不光役畜了,人也不好受,“呸呸”声响个不停。
有人拿手去遮掩鼻孔,长槊也持不住了。
“啊呀!”一名驭手痛苦地倒在地上。
他刚想去安抚拉车的驴子,结果被踢到了。
驴车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冲了出去,站在上面的几名军士东倒西歪,叱骂不已。
就像是传染病一样,役畜焦躁痛苦的叫声此起彼伏,队列渐渐开始凌乱。
“哗啦”两辆车撞在一起。
原来是前面那辆车的役畜不肯走了,结果被后车“追尾”,再后面一辆骡车直接冲出队列。
“定是夏贼之计!”刘捍大吼一声。
风沙涌入,直接将他后半句话给堵在了嘴里。
“嗖嗖!”十余支羽箭借助风势,狠狠地钉在车厢之上。
有头牛被射中了,痛得发狂,直接不管不顾冲了起来,有些军士猝不及防,直接给撞到,惨叫连连。
而这头牛的盲动,也带动了其他役畜,整个车队一片凌乱,人仰马翻。
“怎么让夏贼摸到近前了?”刘捍怒问道。
“太乱了。”有人答道。
有下级军官自发地集结了一些弩手,往羽箭飞来的方向攒射,风沙中隐隐传来一些惨叫。
“轰隆!”一辆牛车横着冲过,将弩手们撞得东倒西歪。
马蹄声已近在耳边,车队右侧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豁口。
这其实还可以弥补挽救,只需有军士赶过来,执长枪列阵,以弓弩为辅,便可将其堵住。
但现在车队有些混乱,军士们四处躲避发狂的牲畜,乱做一团。
不过汴军下级军官的主观能动性还是很好的,有人带着一些军士,气喘吁吁地爬过粮车,向豁口赶去。
“嗡!”一片箭雨落下,刚刚爬过辆车的十余名军士惨叫不已。
“轰!”第一名骑兵冲了进来,手中铁槌砸下,一名汴军士卒悄无声息地倒了下去。
但营地太乱了,不利于汴军布阵,同样也不利于骑卒冲杀,因此只有少数人跟他冲了进来,乱砍乱杀。
大多数骑兵则在外围驰射,趁着汴军大乱的有利时机,将铺天盖地的箭雨送过去。
朱友让直接钻到了辆车底下。
刘捍大吼一声,带着亲兵冲杀了过去。
一兵举起长柄斧,将刚冲进来的骑卒打落马下,一人上前,手起刀落,将其斩杀。
“不许退!”刘捍捡起根被人遗弃的长槊,打落了一名夏军骑兵。
那名骑兵看起来比较勇武,飞快起身,不过又被突袭而至的钩镰枪勾倒在地。
“噗!”一矛将其钉死在地上。
箭雨越来越密集。
刘捍的甲胄上像长了曾白毛一样,他又冲到一处,捅死一名夏军骑兵,怒问道:“弩手呢?把夏贼赶回去啊!”
没人回答。
大部分弩机都放在车驾上,此时这么乱,谁能找到?已经有人翻过大车逃跑了。
“嗡!”又一队骑卒穿过田野,绕到车队另一侧,连连发箭。
腹背受敌!
崩溃先从一角开始,随后蔓延到整个车阵。
有豪勇的汴军士卒仍然依托大车,用步弓还击,也有甲士挥舞着长槊,拼死战斗。
但建制已乱,没有配合,抵抗不成体系,自然收效甚微。
大势去矣!
随着部分夏军骑卒下马,整队冲杀过来,这支汴军的覆没已不可避免。
折嗣裕站在风沙之中,静静地看着。
良久之后,他叹了口气:“缺骑马步兵。”
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