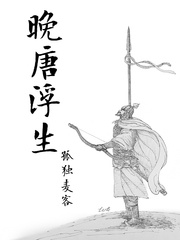倒是随意摆放的麻布炸药包,显得十分丑陋,一看就不是啥好东东,大概在女真人眼中,顶多也就是如破棉絮一般的东西,反而未见丝毫被动过的痕迹。
对此,重真却只是笑笑,道了声“意料之中”,便提醒伙伴们绑好火药包,直至回到大明境内,都不要解下来,便率队退出辽阳,往沈阳进发。
虽然只有两天的接触,还多半是在醉眼朦胧的状态之下,可黄重真这行来自宁远的大明使者,还是给辽阳城的后金贵族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据他们观察,这行来自于辽东关宁的大明军人,虽然成军也就一两年的时间。
但,比之以往的明军,确实有所不同。
尤其是那个国字脸型的少年,虎头虎脑,猿猴的手臂,老鹰的手爪,初看像个愣子,却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不凡之处,展现出来。
“剑眉星目,笑容憨厚,眼神清澈,面色带点儿忠勇的黑,酒量很好,会治醉酒,还会治病,本王的隐疾……咳咳……总之多好的少年啊,可惜,可惜。”
于是,经年之后,当黄重真为救大明信王朱由检,从而命丧大火的消息。
从大明甚嚣尘上传至后金时,济尔哈朗振腕叹息之余,仍对这两天逢场作戏一般,却又入戏颇深的接触,念念不忘。
尤其,是脸上那滩像是鼻涕干了之后的糊状物,实在是令他感到很恶心。
“这就是那家伙的鼻涕啊!恶心死本王啦!”
在辽阳彻底地消失于视线尽头之前,一行少年回头对这座昔日的汉家大城,以及埋骨戚家军与白杆兵忠魂的浑河之畔,投以了深沉的一瞥。
敢于抗争的几乎都被杀光了,大明收复辽阳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即便是宁远这样的大捷,也紧紧只能在这些只想活下去的汉农心中,泛起一丝淡淡的涟漪。
再见了,沈阳,希望再来之日,便是大明全力反攻辽东之时。
北出辽阳渡过太子河,继续北上,再渡浑河,便是沈阳了。
因此,从辽阳通往沈阳的路程,实际上就是在辽沈平原上,欣赏沿途风景的过程,但想象当中阡陌交通的庄稼生长盛况,以及秋收的盛况,并没有多少。
也就刚出辽阳那会儿,在太子河畔看到了不少正在收获的农奴。
然而,在他们沧桑的脸上,看不见丝毫丰收的喜悦,因为他们是被奴役着的。
并且地里的庄稼,长势也不怎么好。
毕竟,这些农奴地位低下,口无余粮,家无余财,还动辄就有被监管的八旗兵鞭笞打杀的风险,哪还会有辛勤劳作的积极性。
大多数的上好的肥田都是荒废着的,白白便宜了荒芜的荒草。
华夏的少年们自懂事那天起,便对田地有着极深的情感。
这是融于骨血当中的,天生便自娘胎里携带而来,只是要到懂事之后,才逐渐开始决心。
尤其,他们最是清楚在山丘遍地的关宁地区,那些隶属于关宁军的青年老汉老妇们,是怎样携带着他们的童孙,在山地之间艰难屯田的。
因此,看到如此多的良田竟就这样白白地荒废着,哪有不无限心疼的道理。
“真是暴殄天物!狗日的女真人既然不会种地,占那么大的一片地儿做什么?真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还不如还给我们汉家子呢!”
便连大少爷出身的吴三桂,都对此唾骂不已。
黄重真趁机对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道:“华夏民族是勤劳的民族,走到各地都没有荒芜的田地。尤其是在北方,没有半亩抛荒的田,农民们都把土地庄稼伺候得很好。
但前提就是,那些当官的还有我们这些当兵的,要把这些田地守护好。白山黑水间的肥沃土壤,是我们自己弄丢的,怨不得人,女真人也不会无端端的将之还给我们。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抢回来。”
这番话,黄重真其实说得很随意。
可吴三桂却听得很认真,难得地听进去了,倒让前者颇感意外,也很是欣慰。
八月的辽东,秋意越发浓了,便连这些荒草也逐渐成了一望无际的金黄,倒也别有一番狂野的风景。
这样的情景,倒是在高科技极度发达的22世纪,绝难瞧见。
荒地还成了许多小动物的家园,经常有小家伙们窜出来,或立刻就被惊了回来,或站在小路中间,与一群少年傻乎乎地面对面。
偶尔遇到一些规模庞大的动物群,倒像是两军对峙一般。
秋阳甚好,秋高气爽,层林尽染,叠翠流金。
这段发生于谍战后金之旅的赶路时光,倒成了黄重真来到关宁之后,堪称最优先的一段旅途了,也终于将他两世的孤独创伤,逐渐地抚平了。
当又一日的夕阳快要西下的时候,再渡浑河之后又往北走了一段路程的少年们,终于在被夕阳拉得老长的身影当中,抬头看到了沈阳隐约的轮廓。
都司祖大乐抹了一把乱糟糟的大胡子,戟指前方,喝道:“快看,那便是建奴的所谓盛京——沈阳了,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一众少年尽皆聚目远眺,只见沈阳虽在夕阳的照样之下金光闪闪,却并没有生机勃勃之感,反而隐隐透出了一股剑拔弩张的沉闷之气。
“走吧,赶在天黑之前,先入城再说。”黄重真出声制止了小家伙们兴奋而又担忧的七嘴八舌,与祖大乐周吉大牛等人并着肩,率先往沈阳行去。
在大势面前,个人的荣辱与生死,显得那般微不足道。
尤其是对于底层的百姓而言,但凡遇见所谓的历史大势,便更加显得他们犹如蝼蚁般卑微,在这大局之中,无论天灾还是人祸,都是令他们陷入劫难的深渊。
十多年来,来自大明腹地的无数“个人”组成了一个个军团,奔赴辽东与后金血战,却又纷纷折戟,鲜血流淌,令黑土地变得更加深沉沧桑。
然而,当太多个人的荣辱与生死,都无法被顾忌的时候。
所谓的大势,却反而显得那般无足轻重。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老百姓仅仅只是为了一口饭吃,都想打破这所谓的大势。
“去彼娘的天下大势,爷爷只想吃口果腹之饭,也为儿孙争一口饱饭吃。”
老百姓的心声,其实真的很简单。
无论哪个时代,但凡身上烙有“百姓”这个标签的人,所求者,仅此而已。
只是大多数时代的大多数当权者,都因各种各样的事物遮蔽了眼睛和耳朵。
也有充耳不闻,视若无睹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实在是个很简单易懂,却又十分微妙,十分矛盾的命题,无论是哪个年代,无论生产力多么发达,都未能完美而又妥善地得到解决。
在辽东大地上的接连失利,让大明损失了太多的精锐力量与银钱,以至于,似乎都有些压不住关内那些,越来越纷繁的山匪流寇之乱了。
加上连年的天灾,以及混乱不堪的内政,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朝廷可以收租的人口与土地,都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饿肚子。
在饥饿的驱使之下,流民越来越多,饿死的也越来越多。
于是越来越多的饿肚子的流民为了活下去,便在有心人的挑动之下,或主动或被迫地变成山匪流寇,就像蝗虫白蚁一样,四处就食掠食。
泱泱大明,雄兵百万,这几年竟也免不了拆东墙补西墙,略显焦头烂额。
可即便如此,大明仍是被整个亚洲所承认的中原正统王朝。
无论朝鲜日本,还是南洋诸国,便连后金,虽在战场之上取得了许多胜利,却非常渴望在邦交之上,得到大明的承认。
“奴酋在对待大明的问题上如此残酷与歇斯底里,除了七大恨的原因之外,大概也有这种令之恼羞成怒的情愫,在他自卑的心理作祟吧。”
遥望着沈阳的西门越来越近,黄重真便以这番对于奴酋的评价,结束了对于历史大势的评判。
因此,当沈阳方面得知大明竟主动遣使而来的消息之时,无论是哪个贵族,都在短暂的惊讶之余,就变成了十分的欣喜。
其中,尤以二贝勒阿敏为甚。
因为,自从济尔哈朗外调辽阳之后,他便在黄台吉的咄咄迫人之下,直感觉压力倍增,时至今日,便连转圜的余地都所剩无几了。
而大明使团的到来,无疑能帮助他分散黄台吉的精力,给予他歇口气的时间与空间。或许,因此而迎来扭转乾坤的契机,都并非没有可能呢。
因此,阿敏上下奔走,倒成了最热衷于大明使团到来的人。
黄台吉与阿善错愕之余,便也乐得轻松,只冷眼旁观,且看他如何蹦跶。
济尔哈朗紧接着送来的情报,倒是让黄台吉与代善心中大定。
“不求议和,但求修好。”
这不正是大金现时最希望的么?所谓正中下怀,大概便是如此吧?
届时,等大金渡过汗位交接的关键时期。
无论是谁登上汗位,新的大汉无论是要立威,还是要重组八个部落间的利益分配,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重整军力再攻大明,都是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