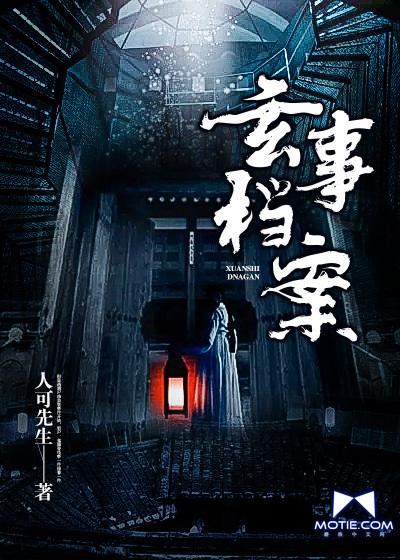毒蛇一样的黑影从两人之间迅速穿过,蔡凡还没来得及出手,那黑影暴露在烛光之下“吱”的一声,眨眼间便缩回了黑雾之中。
苏国忠一把爬起来,心有余悸地问道:“那是什么东西?”
蔡凡摇摇头,刚刚太紧急看得不是很清楚,但那东西好像是一条舌头!这时,那催命一般的歌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了,烛光圈子外面再次陷入了死静。
蔡凡有点紧张地瞄了一眼手中的丁火蜡烛,估摸着还能烧一会,但蜡烛熄灭之后就难办了,那东西应该畏惧烛光,这会儿正隐藏在黑雾之中伺机而动。
“帮我把手脚找回来~”
幽怨凄厉的声音不知道从哪里又再传来,苏国忠咽了口吐沫,低声说道:“这样也不是办法啊,我来试一试它。”
收起手中的那面铜镜,左手掐了个天师决,举起手中的符咒,嘴里急念:“受命于天,上升九宫,百神安位,列侍神公,魂魄和炼,五脏华丰,百醅玄注,七液虚充,火铃交换,灭鬼除凶,急急如律令!”咒语念完,夹着符咒的右手一挥,三张符咒闪起黄光化为杀鬼利箭,“唆唆~”几声急响,冲入了黑雾之中。
黑雾在这一刹那受到了影响,忽然就翻滚动荡,搅起阵阵阴风,但仅仅如此,三道杀鬼符如泥牛入海,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苏国忠脸色一变,又是这种情况,昨天那人皮鬼一般的东西就已经够厉害了,这只好像比昨天那只更厉害,心里顿时没了底。
“你居然不肯帮我,居然不肯帮我……”黑雾之中,刚才唱歌的那个女声忽然来回地叨念着,但这时声音听着不再优美,而是刺耳渗人,刺得蔡凡两人耳膜生痛。
在烛光圈子外面,渐渐地现出一个东西来。
那是一个身穿单薄黑色戏服的光头女人,面色青白,泛着一层惨绿幽光,七孔流血,却在阴测测地笑,渗着血的双眼死死地盯着蔡凡两人;最可怕的是这个女人的衣袖里空荡荡的,随着阴风在飘荡,身下也没有双脚,而是插着一根长长的木棍,它整个看上去就像一根棍子般竖在地上。
这个女人被齐根砍了双手双脚,穿在了一根棍子上!
见到这个东西,感受到那阵让人心惊胆跳的阴煞气,蔡凡两人心跳都加快几拍,额头冒出了汗。蔡凡更是心想,这东西快赶得上传说中的千年厉鬼了吧!两人忽然明白之前那种“咚咚”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了,那是这个女人身下的棍子杵在地上的声音!
这是——人彘!
这时,也许是蜡烛快烧到头了,也许是邪祟现身搅起阵阵阴风压制了烛光,光圈正在逐渐缩小!
蔡凡又再瞥了一眼手中的蜡烛,一咬牙,左手举着蜡烛,先是掏出三张驱邪化煞符扔出去,三张符咒离手随着口中“急急如律令”化为三道火蛇飞去,同时,右手持雷火桃木剑,脚下踏驱邪罡,飞快朝那人彘邪祟杀了过去。
蔡凡一动,光圈也移动,苏国忠不敢让自己暴露在光圈之外,也赶紧脚踏七星罡,举起铜钱剑,跟在蔡凡的后面。
两个踏罡的法师气势汹涌,头顶那盏命灯亮得让人彘稍微斜过眼睛。两人的脚步飞快,烛光光圈也移动得飞快。
三道火蛇就像之前苏国忠扔的符那样进了黑雾范围就熄灭不见了,而且人彘看上去根本就动也没动,无论蔡凡两人多快,它永远都在光圈的边缘,两人手中的驱邪法器想碰到它看上去简直不可能。
这时,蜡烛快烧没了!
蔡凡额头在滴汗,忽然嘴里发出一声清咤,声势逼人,紧接着掐了个手决,急念道:“太上老君教我杀鬼,与我神方,上呼玉女,收摄不祥,登山石裂,佩带印章,头戴华盖,足蹑魁罡,先杀恶鬼,后斩夜叉,急急如律令!”
这一刻,手里蜡烛的烛火似乎被滴上了火油一样,身周刹那间亮如白昼,黑雾被驱散到远处,烛光一瞬间便罩住了人彘,同时,蔡凡脚尖点地整个人一跃而去,矫健的身形迅速滑过他和人彘之间的距离,手中的桃木剑狠狠地一刺!
苏国忠不敢落后,眼看机会稍纵即逝,这样的生存机会不敢退缩,咬破指尖,使劲在铜钱剑上一抹,大喊一声:“急急如律令,去!”铜钱剑像一支箭矢般飞去,后来居上越过了蔡凡直指人彘,自己也掏出两张杀鬼符飞快地冲过去。
两位法师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只求在烛光熄灭之前干掉这鬼东西。
人彘在被烛光笼罩的那一刻就显得十分痛苦,摇头尖叫着浑身上下都冒着青烟,身下的棍子杵在地上“咚咚”直响,不断往后退只想逃离烛光的笼罩,但两人杀招已经逼近,人彘凶狠地鬼叫一声,血淋漓的嘴巴张开来,口中舌头竟然像毒蛇出洞般飞弹而出,一下子将苏国忠的铜钱剑扫落地,不过舌头被削断了一截,在“滋滋”冒着青烟。
这时,蔡凡杀到了,桃木剑眼看就要刺在人彘额头那,周围却忽然黑了下来,阴风瞬间夹着黑雾疯狂围拢过来。
“呀~”
人彘发出一声让人胆寒的凄厉惨叫,周围的环境再次陷入凝固般的死寂。
苏国忠大为紧张,夹在手中的符咒一捻,火光亮起映着他和蔡凡两人的面庞显得有些阴森,但光亮照不出身周三步。
“怎么样,干掉了吗?”苏国忠额头上全是汗,小声问道。
蔡凡摇摇头,“黑雾还没散,你说呢。”同时瞥了眼地上的一截衣袖,心里叹息,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
“怎么办?”
“把符火灭了,这样我们也看不到它在哪,反而会影响我们的感觉。”蔡凡也没说怎么办,桃木剑平举横在胸口防备着,这时候他反而比之前要平静不少。
符火熄灭了,眼前再次陷入一片黑暗。
“喈喈喈~”,黑暗中,人彘的怪笑声十分渗人,它似乎很愤怒,周围的黑雾也受到影响,翻动得更加快了。
蔡凡两人背靠着背,提起十二分精神,眼睛直直地盯着前面。
忽然,一个鬼影“呼”的一声从旁边飘过,两人赶紧转身,但它很快就消失了,紧盯着周围,那东西忽然又从身边飘过,两人赶紧又转身。就这样,人彘时不时地从身边飘过,转了几圈之后,蔡凡两人都有些恼火,这跟耍猴子有什么分别!
就当两人以为又是对方的虚招时,一道黑影混杂在翻动的黑雾之中朝苏国忠卷来,虽然看得不清楚,但他手中的动作不慢,铜钱剑一挥迎了上去。
“啪”,人彘“吱”的一声怪叫,紧接着便是叮叮当当的铜钱落地声,这一下竟然将五帝钱穿起来的铜钱剑抽得崩碎。
苏国忠喘了一口气,又从袋子里掏出一把铜钱剑,蔡凡有些惊愕,刚刚丢掉一把,崩掉一把,居然还有,没忍住问道:“你还有几把?”
“就这一把了,这又不是街边的冒牌货,我这几把都是开过光的。”
蔡凡还想说什么,这时,那道黑影冷不丁的从斜地里朝他卷来,蔡凡一剑刺去,但是只堪堪刺中一点儿,被那黑影抽在肩头上,整个人被抽了一个趔趄,痛得他闷哼一声。
人彘没有了手脚,光凭借着浓重的阴煞气就用一条舌头都能杀人,这东西真是凶得让蔡凡无语。
虽然很想干掉它,但这样的情况对蔡凡两人非常不利,那鬼东西时不时就这样来一下,手里的符咒、法器都发挥不了威力,很快两人就都被那诡异的舌头抽了几下,疼得龇牙咧嘴。
“啪”,苏国忠最后一把铜钱剑崩碎,他赶紧朝蔡凡喊道:“蔡师傅,给我点东西。”
蔡凡挥着桃木剑,“你用铜镜啊,用符啊,给你了我用什么?”
苏国忠没办法,一只手举着铜镜,另一只手夹着符咒,但用起来很不方便,有一次如果不是蔡凡救得及时,差点就被拖了过去。
诡异的舌头围着蔡凡两人飞舞,角度刁钻,袋子里的驱邪符、杀鬼符、五雷符、真君符、丁甲符、开山治煞符甚至去病符、净坛符、镇宅符都扔了出去,但这就跟在水里点火一样,符火根本对付不了周围那浓重的阴煞气,甚至人彘都敢用舌头去抽符火,如果不是咬着牙坚持着踏罡,估计早就被阴气侵蚀了心神,更加不用说想干掉那鬼东西。
才过了十来分钟,两人已经浑身大汗,气喘吁吁,不但体力开始不支,身上的伤也越来越多,更要命的是袋子里的符咒快见底了,而且随着两人气势的下降,阴气渐渐地顺着受伤的地方侵入体内。
楼外,老太他们正站在一起紧张地观望着,但整栋楼还是处在黑雾之中,四楼处那浓重的黑雾没有丝毫消退的迹象。
“师父!”虽然蔡凡两人上去的时间不长,但陈华芳非常担心,又不知道怎么办。
老太神色凝重,估算了一下时间,从两人上去到现在大概过了二十几分钟,放松一下捏得发白的手指,说道:“他们才进去不久,再等一会看看。”其实她也等得非常不耐烦,胸口好像有一口闷气在压着,但这里就她在镇场,总不能自乱了阵脚。
大楼里,蔡凡浑身难受,有点不受控制地想打寒颤。
苏国忠已经控制不住在发抖了,牙齿打颤地说道:“蔡,蔡师傅,想个办法吧,你的墨斗呢?我们像昨天那样再来弹一次。”
蔡凡喘了口气,回答道:“在这样浓重的阴气里你敢分开?这东西的舌头两下就能把你撕碎了。”
苏国忠急得大叫道:“总不能等死吧?”
蔡凡刚想问你师父会不会来救我们,人彘的舌头忽然就卷住了苏国忠的脖子,一下子将他拖入过去。
蔡凡眼疾手快,向前一扑伸手抓住他的脚踝,这样狠狠的拉扯下让苏国忠顿时就翻了白眼,拼命地拉扯着那条舌头,但怎么也扯不开。蔡凡赶紧又是一扑,一剑削断了那舌头。苏国忠觉得脖子一松,扯下那截缠在自己脖子上的舌头,死命地喘着粗气。
蔡凡问道:“没事吧?”谁知苏国忠还没回答,只是惊恐地看着他的背后,只见那人彘在蔡凡背后露出了一张恐怖的脸。蔡凡心道糟糕,回头就是一剑,但人彘比他更快,舌头卷着蔡凡的手臂像一条毒蛇一样一直往肩膀上爬去,自己的手臂好像快要断了一样的疼,感觉人彘在收紧舌头而且要往外拉,蔡凡瞳孔都缩了缩,这是要把他整条手臂都扯下来啊。
来不及多想,左手掏出那把珍藏的小扫把狠狠地朝人彘扫过去,那鬼东西也知道厉害,但舌头来不及缩回来,居然闭口一咬就把舌头咬断,飞快地缩回到黑暗里避开扫把的横扫。
蔡凡心道好险,刚刚差一点就变独臂人了,扯掉缠在自己手臂上的舌头,这东西滑腻腻的,一离开人彘就变得腐败恶臭难闻,让人一阵恶心。
“你还行吗?”蔡凡朝苏国忠喊道。
说话间,苏国忠又被舌头抽了一下,撒出几张符咒逼退它,已经站不稳了,摇摇头,“不行了,这东西的舌头究竟有多长啊,快想办法吧,你那扫把给我用一下,或者你的桃木剑给我吧。”
蔡凡想了想,把桃木剑递给他,举着小扫把问道:“你师父呢?难道要我们自求多福?”
苏国忠握着桃木剑稍微镇定了些,说道:“我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来救我们,而且她年纪大了,我师妹又不中用,你快些想个办法吧。”
蔡凡暗骂一句,你大爷的,这回要被坑死了。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了。”只见蔡凡忽然深吸一口气,然后扯着嗓子大声喊道:“狗子,快来救命啊!”
苏国忠一听,差点没忍住要破口大骂。这地方被煞封住了,你喊什么外面也听不到,而且那条破狗来了又能怎么样。